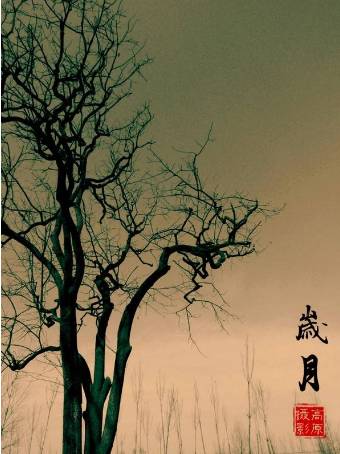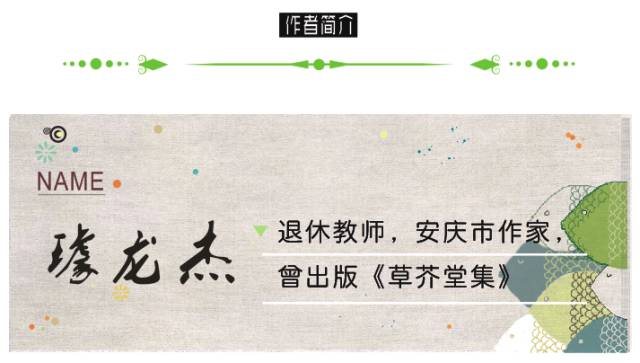2012年,桐城璩氏世德堂修谱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。居住在当地的族人们都登记得差不多了。由于我是编辑之一,身负重任,压力山大。父亲别的不当心,最使他放心不下的就是璩楼南坡公这一房。璩楼在金拱镇西湖村,1956年以前这里归桐城县,后划归怀宁县管辖,也是璩氏族人比较集中居住地。这里的族人与我房头世系比较接近。可以这样计算,在元末明初从江西瓦屑坝迁桐第一代算起,我与璩楼第九代是同胞弟兄。他们是长房伯盤公,我们是小房伯康公。到我爷爷这一代是第十八世,中间相隔八代。虽然早已出了五服,但在桐城整个璩氏家族当中,也算比较亲近的了。父亲为什么惦记着这一房呢?说起来有一定的渊源。璩楼第十七代有个璩志学,名筠字南坡一字筱楼,县丞令。清同治十二年出生。在光绪年代后期乃至宣统和民国初期,他在西乡黄马河保是个响当当的人物。既在政府有职,又是这一带璩氏家族之中问事之人。其他姓氏的人都不敢小看他,在乡间也留有许多佳话。说来话长,1949年之后,这一家人销声匿迹,人间蒸发。其时,南坡公已过世,仅剩小夫人。周边乡民不知她姓甚名谁,又是个外乡人,再加上她是长辈,大家都喊她侉奶奶。一则可能她属于北方人,我们家乡对北方人都称“北方侉子”;二则也许她生得人高马大的缘故。所以,得此雅称。 父亲生怕他这一房修谱漏掉了。时不时地问我: 找没找到线索?我说没找着。他就喃喃自语: 那就怪了,南坡公有个儿子,比我大几岁,我们当年在天城读过书的,算来是同学啊。提起这件事,父亲向我讲述了他们当年读书时的一件往事: 五月往的一个周末,天下暴雨,放学回家的路上,大沙河突然涨水了。父亲当时年幼胆小,是南坡公的儿子背起他摸水过河的。璩楼离白果过河的地方没多少路,天黑了,衣服又湿了。父亲那天晚上就在他家过夜的,第二天才回家。由于我爷爷是个监生,属于读于之人,在那个年代,也算是家族之中的先生。他比南坡公小十六岁,后期黄马河保这一带族中诸事,都是我爷爷出面。于是,我们两家就有来往。当年,我父母结婚的时候,侉奶奶上门来送过贺礼。没有修谱的时候,父亲未提及此事,启动修谱之后,他就不止一次提起这件事。我知道,其目的就是要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将南坡公这一房从谱上漏掉。修谱搜集资料的这几年,我骑着一辆摩托车,经常穿梭于桐、怀两县交界处。璩楼也不知去了多少趟。当然,也不是为了南坡公一家的资料。然而,世事沧桑,偌大的一座村庄,全被夷为平地。被土地置换工程,让整个璩楼老房屋已不复存在,平整成一片片土地,全部种上了玉米。在清朝年间,村庄被称为楼的都有一种特殊性,起码比一般村庄要高出些档次。比如,我在《六尺巷文化》平台上曾刊出“潘赞化与璩方氏”的文章,那里面的潘楼与方楼与一般村庄就有区别,它们就有名气得多。璩楼也不例外,民间传说: 璩楼的大门头子,是伍经阳(也许不是此三个字,是有名的地师)测向定夺的。所以,这里曾经人文荟萃,人才辈出,尽出读书之人。上溯桐城璩氏族谱,璩楼主持人几乎占了整个谱的半壁江山。乾隆二修是桐岡公,梅芳公二修誊稿三修为户尊,克锐公总稿。四修光烁公创新改革,欧、苏兼顾式。让周边其他姓氏惊叹不已。他们皆为绍绥公后裔,与南坡公同出一脉。再从近代来说,戴娇倩系出璩楼,台湾璩美凤的祖父同样出自璩楼。还有许多可能未被发现。没有了璩楼,族人们各奔东西,有的外出定居,有的在城里买了房子。每次去寻找族人,大都一问三不知。对南坡公这一房,还有一个特殊原因: 解放初期,他家成份很高,儿子早年外出一直未归。那个年代,像这类人家是倍受歧视,人们怕惹麻烦,牵涉到他家都是三缄其口。就是亲房本户,都会绕弯子避开的。几十年过去,慢慢淡出人们的记忆。后来,我就从周边其他姓氏老年人那里打听,都说是有这个人,但他的后人却没见过,在什么地方?不甚了了。修谱要定稿了。父亲问我南坡公这一房怎么定?我说按老谱上来,上面写着什么就照寻什么。由于我璩氏世德堂六修谱断代,此次七修只能按五修顺延。五修又是宣统二年修的,距今百年以上,几乎间隔四、五代人。找不到祖上的很多,孙不识祖的也不少。尤其在五修以后外迁的族人,那个年代,有的是挑着箩担背井离乡的,只顾活着的人是如何活下去,哪里还顾得上祖先不祖先呢。在五修谱上,南坡公只有自己和原配夫人汪氏的信息,而且汪氏已故,卒葬皆有记录。既无侉奶奶的片言只字,又无生子的任何信息。怎么办?父亲对我说: 南坡公有儿子这是实实在在的,我接触过,你就记上他的儿子,也不至于让这一房断掉。父亲的心情我当然理解,我肯定不会草率行事。我决定抽空再到璩楼隔壁村里去问问人,事前也听到有关南坡公后人的一些传闻。结果,还真获得了一个重要信息,说是这家有后人在内蒙古。传闻是有原因的,多年前,有内蒙方面来过信,联系故乡人。皆因行政区划的变更,地址对不上号,年代久远,往日亲朋故旧已过世,来信又没到璩楼,落到另外一个村里,这个村里人又不知道璩楼有这么一户,真是阴差阳错,失之交臂。来信长期无人接收,只能打回原址。这也算寻根问祖,但此次是不了了之。大概也在2012年底,在桐城璩氏家族群里,有人发了一则信息: 有一个老人,年轻时就参加了国民革命军,曾在黄埔军校某期集训过。老家是桐城人,名字叫璩宗重,寻求家乡信息。那时,我对电脑操作才刚刚起步,半拉子水平,问别人,别人说是转发过来的。我想: 解决这个问题的突破口还是问我父亲,只要璩宗重是南坡公的儿子,这个问题就有了转机。幸亏问得及时,我父亲2013年5月去世,享年91岁。此前我问他,他回忆说: 念书时好像不是这个名字,当年好像听到叫诗重。这不就行了嘛,他是诗字辈,起码接祖上是不会错的了。按道理,我们应该继续查下去。但修谱这项工程已拖了这么多年了,牵涉外地族人的资料进展缓慢,收效甚微。再加上方方面面的原因,个中苦衷真的是一言难尽。谁也没有能力再力挺外出,耗资巨大。如果查找没有效果,谁又来担当这个责任呢?再者,成谱印刷又是整体工程,一旦开机不可能停下等你再编辑的。更不可能为了这一户,再到內蒙古去“大海捞针”吧。于是,南坡公名下有宗重出现,在五修谱的基础上加: 继娶氏生年不详,当地人称侉奶奶卒葬亦不详。宗重公名下: 生年、娶妻、生子不详,居内蒙古,情况不明等等。但愿皇天有眼,祖上有德。我只能寄希望于族中后起,下届修谱来完成这个使命吧!2016年6月11日上午,我突然接到西湖村原书记汪经富的电话,他说: 又有璩楼外地你的本家寻根问祖来了。我想,只有找你了。这个“又有”说明不止一次了,那年戴娇倩的母亲璩伟萍为自己父亲坟墓安碑,带领一帮上海族人回璩楼认祖归宗,也是找这位汪书记的。汪经富现在已故,他真的是一个有人文情怀的基层领导。他将客人指到我家,一行四人,开着一辆轿车,是内蒙牌照。不用介绍,我已经知道他们是谁了。带队的是一位长者,墩墩实实的个头,北方人固有的肤色。但他眉宇间和那未曾开口先有笑意的神态,好像我们曾似相识一样。无论他的母亲是哪里人氏,或者说他出生在那遥远的北方,长期生长在异地他乡,那潜藏在骨子里的父辈气质都无法掩盖。尽管我没见过对方的上辈人,但仅凭我长期接触家族中的诸多长者们,我可以断定此人是宗重公的后人,就不知道怎么称呼。通过介绍,长者叫书志,比我长一辈,按桐城人的称谓,我喊他椒椒。但他比我小一岁,1948年出生。他客气,喊我老哥。同来的有他的夫人,与我老伴同龄,1950年出生。典型的北方女人气质,壮实,富态,沉静而又端庄。也许是坐车时间太长,有些疲倦。汽车是从包头开过来的,乘坐几十个小时,真的不简单。司机是他们的孙子,名叫泽元,身材魁梧,白白胖胖的小伙子。一个人驾驶,丝毫不见他有旅途的疲劳。还有一个是泽元的大学同学,安庆人。此次南下,一则到老家寻根问祖,无论如何要完成上辈的遗愿,二则送泽元的同学回安庆。老家在璩楼,离这儿还有七至八公里路。首先,将谱事处理好再说。找到璩楼这一卷,当翻到南坡公这一页时,宗重记在他父亲名下。再查到宗重公,虽然没有娶妻生子的状况,但记有后人居住在内蒙古,就凭这一条足以让书志椒椒非常感激。他问我怎么知道这则信息?我说根据两点: 一是邻村人的口传,二是根据网络上发出宗重公的名字。我就将自己父亲少年时代与宗重公的交集,向他介绍一番。他感慨万千: 我们真有缘分,祖上的世交,百年沧桑,其后辈又相聚在一起,真的让人匪夷所思。短暂的时间,书志椒椒只将自己的奶奶向我介绍了一番。被乡间称为侉奶奶本姓高,扬州人,父亲宗重属她所生。其实,他根本没有见过自己的爷爷和奶奶,这一切都是他父亲告诉他的。因为,他父亲从民国二十几年外出从军,一直未回过故乡,哪里还顾得上家里的事呢。由于时间仓促,他们上午必须要赶到安庆。千里迢迢来寻根问祖,连一顿便饭都没招待,我们的先人泉下有知,肯定会指责东道主寡情寡义的。然而,书志椒椒今天特别高兴,我把他家信息全都续到谱上。按他的说法,这比吃什么都是值得的。我们七修谱是2014年底竣工,2015年清明节全部发放到位。这个时段再来补录信息,是不是晚了一点呢?然而,我们事前就已经预料到有这种情况发生。所以,凡在后期补录的信息,一律录到祠堂珍藏的那套“天字号”的总谱上,以便将来八修不至于再遗漏。当然,南坡公这一房的补录工作,我后期特地赶到祠堂将其完善了。按理,此事应该结束了。哪里知道,2017年8月8日,大概是下午,还是那辆轿车,突然又停在了我家门口。从车里下来五个人,书志椒椒夫妇,司机还是泽元那个小伙子。另外是书志椒椒的女儿母女二人。他们又是从包头开车过来的,我说: 小伙子你真不简单啦。他却说: 我从十几岁就开车了,这不算什么。
父亲生怕他这一房修谱漏掉了。时不时地问我: 找没找到线索?我说没找着。他就喃喃自语: 那就怪了,南坡公有个儿子,比我大几岁,我们当年在天城读过书的,算来是同学啊。提起这件事,父亲向我讲述了他们当年读书时的一件往事: 五月往的一个周末,天下暴雨,放学回家的路上,大沙河突然涨水了。父亲当时年幼胆小,是南坡公的儿子背起他摸水过河的。璩楼离白果过河的地方没多少路,天黑了,衣服又湿了。父亲那天晚上就在他家过夜的,第二天才回家。由于我爷爷是个监生,属于读于之人,在那个年代,也算是家族之中的先生。他比南坡公小十六岁,后期黄马河保这一带族中诸事,都是我爷爷出面。于是,我们两家就有来往。当年,我父母结婚的时候,侉奶奶上门来送过贺礼。没有修谱的时候,父亲未提及此事,启动修谱之后,他就不止一次提起这件事。我知道,其目的就是要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将南坡公这一房从谱上漏掉。修谱搜集资料的这几年,我骑着一辆摩托车,经常穿梭于桐、怀两县交界处。璩楼也不知去了多少趟。当然,也不是为了南坡公一家的资料。然而,世事沧桑,偌大的一座村庄,全被夷为平地。被土地置换工程,让整个璩楼老房屋已不复存在,平整成一片片土地,全部种上了玉米。在清朝年间,村庄被称为楼的都有一种特殊性,起码比一般村庄要高出些档次。比如,我在《六尺巷文化》平台上曾刊出“潘赞化与璩方氏”的文章,那里面的潘楼与方楼与一般村庄就有区别,它们就有名气得多。璩楼也不例外,民间传说: 璩楼的大门头子,是伍经阳(也许不是此三个字,是有名的地师)测向定夺的。所以,这里曾经人文荟萃,人才辈出,尽出读书之人。上溯桐城璩氏族谱,璩楼主持人几乎占了整个谱的半壁江山。乾隆二修是桐岡公,梅芳公二修誊稿三修为户尊,克锐公总稿。四修光烁公创新改革,欧、苏兼顾式。让周边其他姓氏惊叹不已。他们皆为绍绥公后裔,与南坡公同出一脉。再从近代来说,戴娇倩系出璩楼,台湾璩美凤的祖父同样出自璩楼。还有许多可能未被发现。没有了璩楼,族人们各奔东西,有的外出定居,有的在城里买了房子。每次去寻找族人,大都一问三不知。对南坡公这一房,还有一个特殊原因: 解放初期,他家成份很高,儿子早年外出一直未归。那个年代,像这类人家是倍受歧视,人们怕惹麻烦,牵涉到他家都是三缄其口。就是亲房本户,都会绕弯子避开的。几十年过去,慢慢淡出人们的记忆。后来,我就从周边其他姓氏老年人那里打听,都说是有这个人,但他的后人却没见过,在什么地方?不甚了了。修谱要定稿了。父亲问我南坡公这一房怎么定?我说按老谱上来,上面写着什么就照寻什么。由于我璩氏世德堂六修谱断代,此次七修只能按五修顺延。五修又是宣统二年修的,距今百年以上,几乎间隔四、五代人。找不到祖上的很多,孙不识祖的也不少。尤其在五修以后外迁的族人,那个年代,有的是挑着箩担背井离乡的,只顾活着的人是如何活下去,哪里还顾得上祖先不祖先呢。在五修谱上,南坡公只有自己和原配夫人汪氏的信息,而且汪氏已故,卒葬皆有记录。既无侉奶奶的片言只字,又无生子的任何信息。怎么办?父亲对我说: 南坡公有儿子这是实实在在的,我接触过,你就记上他的儿子,也不至于让这一房断掉。父亲的心情我当然理解,我肯定不会草率行事。我决定抽空再到璩楼隔壁村里去问问人,事前也听到有关南坡公后人的一些传闻。结果,还真获得了一个重要信息,说是这家有后人在内蒙古。传闻是有原因的,多年前,有内蒙方面来过信,联系故乡人。皆因行政区划的变更,地址对不上号,年代久远,往日亲朋故旧已过世,来信又没到璩楼,落到另外一个村里,这个村里人又不知道璩楼有这么一户,真是阴差阳错,失之交臂。来信长期无人接收,只能打回原址。这也算寻根问祖,但此次是不了了之。大概也在2012年底,在桐城璩氏家族群里,有人发了一则信息: 有一个老人,年轻时就参加了国民革命军,曾在黄埔军校某期集训过。老家是桐城人,名字叫璩宗重,寻求家乡信息。那时,我对电脑操作才刚刚起步,半拉子水平,问别人,别人说是转发过来的。我想: 解决这个问题的突破口还是问我父亲,只要璩宗重是南坡公的儿子,这个问题就有了转机。幸亏问得及时,我父亲2013年5月去世,享年91岁。此前我问他,他回忆说: 念书时好像不是这个名字,当年好像听到叫诗重。这不就行了嘛,他是诗字辈,起码接祖上是不会错的了。按道理,我们应该继续查下去。但修谱这项工程已拖了这么多年了,牵涉外地族人的资料进展缓慢,收效甚微。再加上方方面面的原因,个中苦衷真的是一言难尽。谁也没有能力再力挺外出,耗资巨大。如果查找没有效果,谁又来担当这个责任呢?再者,成谱印刷又是整体工程,一旦开机不可能停下等你再编辑的。更不可能为了这一户,再到內蒙古去“大海捞针”吧。于是,南坡公名下有宗重出现,在五修谱的基础上加: 继娶氏生年不详,当地人称侉奶奶卒葬亦不详。宗重公名下: 生年、娶妻、生子不详,居内蒙古,情况不明等等。但愿皇天有眼,祖上有德。我只能寄希望于族中后起,下届修谱来完成这个使命吧!2016年6月11日上午,我突然接到西湖村原书记汪经富的电话,他说: 又有璩楼外地你的本家寻根问祖来了。我想,只有找你了。这个“又有”说明不止一次了,那年戴娇倩的母亲璩伟萍为自己父亲坟墓安碑,带领一帮上海族人回璩楼认祖归宗,也是找这位汪书记的。汪经富现在已故,他真的是一个有人文情怀的基层领导。他将客人指到我家,一行四人,开着一辆轿车,是内蒙牌照。不用介绍,我已经知道他们是谁了。带队的是一位长者,墩墩实实的个头,北方人固有的肤色。但他眉宇间和那未曾开口先有笑意的神态,好像我们曾似相识一样。无论他的母亲是哪里人氏,或者说他出生在那遥远的北方,长期生长在异地他乡,那潜藏在骨子里的父辈气质都无法掩盖。尽管我没见过对方的上辈人,但仅凭我长期接触家族中的诸多长者们,我可以断定此人是宗重公的后人,就不知道怎么称呼。通过介绍,长者叫书志,比我长一辈,按桐城人的称谓,我喊他椒椒。但他比我小一岁,1948年出生。他客气,喊我老哥。同来的有他的夫人,与我老伴同龄,1950年出生。典型的北方女人气质,壮实,富态,沉静而又端庄。也许是坐车时间太长,有些疲倦。汽车是从包头开过来的,乘坐几十个小时,真的不简单。司机是他们的孙子,名叫泽元,身材魁梧,白白胖胖的小伙子。一个人驾驶,丝毫不见他有旅途的疲劳。还有一个是泽元的大学同学,安庆人。此次南下,一则到老家寻根问祖,无论如何要完成上辈的遗愿,二则送泽元的同学回安庆。老家在璩楼,离这儿还有七至八公里路。首先,将谱事处理好再说。找到璩楼这一卷,当翻到南坡公这一页时,宗重记在他父亲名下。再查到宗重公,虽然没有娶妻生子的状况,但记有后人居住在内蒙古,就凭这一条足以让书志椒椒非常感激。他问我怎么知道这则信息?我说根据两点: 一是邻村人的口传,二是根据网络上发出宗重公的名字。我就将自己父亲少年时代与宗重公的交集,向他介绍一番。他感慨万千: 我们真有缘分,祖上的世交,百年沧桑,其后辈又相聚在一起,真的让人匪夷所思。短暂的时间,书志椒椒只将自己的奶奶向我介绍了一番。被乡间称为侉奶奶本姓高,扬州人,父亲宗重属她所生。其实,他根本没有见过自己的爷爷和奶奶,这一切都是他父亲告诉他的。因为,他父亲从民国二十几年外出从军,一直未回过故乡,哪里还顾得上家里的事呢。由于时间仓促,他们上午必须要赶到安庆。千里迢迢来寻根问祖,连一顿便饭都没招待,我们的先人泉下有知,肯定会指责东道主寡情寡义的。然而,书志椒椒今天特别高兴,我把他家信息全都续到谱上。按他的说法,这比吃什么都是值得的。我们七修谱是2014年底竣工,2015年清明节全部发放到位。这个时段再来补录信息,是不是晚了一点呢?然而,我们事前就已经预料到有这种情况发生。所以,凡在后期补录的信息,一律录到祠堂珍藏的那套“天字号”的总谱上,以便将来八修不至于再遗漏。当然,南坡公这一房的补录工作,我后期特地赶到祠堂将其完善了。按理,此事应该结束了。哪里知道,2017年8月8日,大概是下午,还是那辆轿车,突然又停在了我家门口。从车里下来五个人,书志椒椒夫妇,司机还是泽元那个小伙子。另外是书志椒椒的女儿母女二人。他们又是从包头开车过来的,我说: 小伙子你真不简单啦。他却说: 我从十几岁就开车了,这不算什么。